![]()
在前一篇介紹《細說三國》的文章中,我一直避免提到黎東方寫作《細說三國》的詳細背景,那是因為,我打算要把這本書的序言〈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〉完整地貼出來,由黎東方本人自己來說 。
貼序文的目的,乃是因為想補足簡體版的不足。簡體中文版的《細說三國》,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編者在書前有兩點「出版說明」:
- 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,今合为一册。
- 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,经作者同意,在这次出版时,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、提法稍作修改。因为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,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。
我上篇文章有提到周浩然「細說中國風雲時:黎東方著《細說三國》」介紹文,該文中也提到:
……
但還有不太理想的,由於兩岸史觀的不同(這是官方說法),國內版中刪去了不少借古喻今的章節,也刪掉了一些論及國外的章節,看來便失卻了不少趣味。歷史,最珍貴的地方便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現實生活的反映,作出檢討;然而在一個不太容許批評,更不太容許以史反諷政策的國度中,歷史這一功能便不經意被剔除了。這不是黎東方的錯,只是作為人民的某一程度的損失而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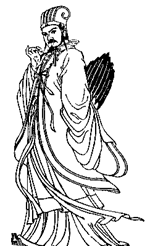 補回失去的,標出新加的
補回失去的,標出新加的
所以,我在整理、還原繁體版原書的同時,比較兩版本間的差異,也是一項頗有趣的事情。而我會想要引用這整篇序言,乃因這序言被刪得最多,使得原本一個相當精彩有趣的故事,變得有點跳躍而不連貫,可說是減色不少。
這〈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〉,應該是全書最晚寫成的,我查了一下,本文刊登在民國六十六年(1977 年)十一月號的《傳記文學》雜誌裡(現收錄於合訂本的第 31 卷 第 5 期 第 23 篇)。而簡體版是出版於 2000 年 10 月,中間相差有二十三年,但由於某些「政治環境與史學觀點的差異」,讓這些文字從較新出版的版本中消失了。
 |  |
在我的繁體版中,我把被刪除的文句加了回去,這部分我用楷體字標明。而簡體版新加的字句(主要是為了讓文章通順,或修正舊版的錯誤,或因兩岸年號、地名等習慣用語的不同,而改用對岸用語),我則用「實心方頭括號」(【】)圈出。也就是說,若要看繁體版文字,就請忽略方頭括號及其裡面的文字;若要知道簡體版的文字,就無視楷體字,只看內文加方頭括號裡的字即可。
為了讓網誌版面不會太單調,以下文章的插圖是我自行加上去的,沒任何特殊意義。
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
文:黎東方
聯副【XX】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「開講三國」的經過,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。我真有點不好意思。怕說得太多了,叫人難以相信。所以,我只想輕描淡寫說一下。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,而今日在臺灣的,人數不在五千以下;我很感謝他們,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,見面的時候鼓勵我。他們甚至「加油添醋」,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。例如,說我講了《紅樓夢》,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。
「紅樓夢」我只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講過一次,但沒有賣票。在重慶公開講「紅樓夢」而賣票的,不是我,而是中國共產黨所捧出來的一位高語罕。高語罕曾經在黃埔軍校,周恩來代理政治部主任之時,當過教官之類的職務。他對馬克思主義知道不多,對紅樓夢知道得更少;他僅僅從所謂唯物史觀的觀點,給紅樓夢中的人物,一一戴上什麼大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、地主階級、無產階級,等等非驢非馬的帽子。中共捧他出來,原是想給我一點顏色看,和我比,看誰的聽眾多,而不在乎票房的收入。結果,來聽的僅有五六十人,而多數是拿了免費招待券入場的。
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,不是我;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。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。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,似乎是我。但是,龔德柏先生說,是他。大概是他,也許還是我,記不清了。
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,可能是馬克.吐溫(Mark Twain)。也許是另一人。讓將來的有心人,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。
我開始講《三國》的一天,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【1944年9月24日】,一連講了十天。地點是在重慶、中一路、黃家埡口、山東省立實驗劇院。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?因為,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,(也是當時名叫藍蘋,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);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,不收場租。

根本,為什麼要講?為什麼要賣票?為什麼不講別的,偏要講《三國》?為什麼要講?是為了賣票。不是為了講而賣票,是為了賣票而講。為什麼要賣票?因為窮。為什麼窮?因為通貨膨脹。戰前,我的一個月薪水,可以買一百雙皮鞋,或四十擔米。到了民國三十三【1944】年,我的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。買了皮鞋,便無錢買米。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。日本人定要侵略我們,我們的政府不得不率領全國同胞起而抵抗。抵抗了七年,民窮財盡;抽不到多少稅,又借不到多少外債,只好印鈔票。鈔票越印越多,物價就越來越高。於是,我兼了三個大學的課;太太作了王泊生那裡的國文科主任,一家七口,依然活得十分吃力。
有一天晚上,太太在「大樑子」(?)劇院的課堂教完了一天的書,擠上公共汽車回到兩路口,我們的家,菜色的臉上添了一層灰白。我突然想起了古書上「窮則變、變則通」那一句話,向太太陳述我的「求變」之意:「這樣下去不行。你會累死。」她說,「你也會累死。那有你這種步行七十里,走到沙坪壩兼課的教授?看你的臉!黑一塊,青一塊,當年白裡透紅的清華少年跑到那裡去了?」(事實上,我去沙坪壩中央大學,不僅步行,而且要爬過一座「金剛坡」高山;陪我爬的是其後頗享盛名的畫家傅抱石。我不是不喜歡乘長途汽車,而是鐘點費減去車費,便所剩無幾,失掉了兼課的意義;因此才捨車而步。)

這真是,「知夫莫若妻」。我直到其時為止,不曾覺察到自己竟有說話的一技之長。我得意之餘,向她說:「我能說話就好。該吃開口飯;而不必一定吃教書的飯。說書,不也是很好麼?」
母親立刻表露了她的興趣。她說:「說書的人吃得好。我小時候,鄰舍住了一個說書的。他家裡天天買肉吃呢。在我們清朝時候,教書的人也窮。可憐的顧老師,過年過節,才買一斤半斤的肉。顧師娘苦了一輩子呢。」(顧老師是我母親小時候的另一鄰居。)
太太說:「說書也得有本事啊。你能說什麼呢?對啦!前幾天有一場電影,演的是美國馬克.吐溫的故事。馬克.吐溫辦印刷廠,破產;異想天開,講演,賣門票,竟然還了債,又賺了不少錢,並且環遊世界,作了旅行演講。我看,你也不必轉說書的念頭了。就試試演講賣門票罷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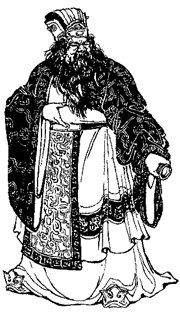
因此,我就決定以演講三國為「入世之媒」,為新的謀生之道。說來慚愧,我對三國這一短暫時期的歷史,並無了不起的研究,只是與極多和我同時代的男性讀書人一樣,自幼便瀏覽了三國演義幾遍,其後也涉獵了三國志與資治通鑑等幾部「正經書」,對演義中的若干說法獲得了若干「折衷」,如此而已。我佔便宜的地方是:曾經在戰前作了一番相當仔細的筆記,也於抗戰開始以後先後在西安的東北大學與成都的中央軍校,講過「三國戰史」。於是,在實驗劇院登臺以後,竟然能夠說得頭頭是道、津津有味,不僅糾正了三國演義,也大膽檢討了平劇之中的若干有關三國的戲。我認為:孔明的年紀比周瑜小,孔明不該作老生,周瑜不該作小生,等等。
值得同情與欽佩的戰時教授如我【當時】,有了免費的場子,【我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,與印刷入場的票。好心的《中央日報》社同仁,特許我先登廣告,後收廣告費。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,後收印刷費。在門口賣票、收票的,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,他們純盡義務,不收報酬。
沒想到,一砲打響,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。第一天,便來了三百多人。每人的門票是法【國】幣四十元(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,是法【國】幣二十元)。一連十天,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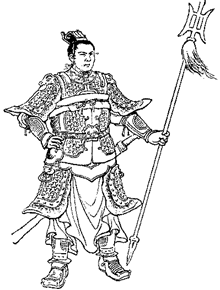
再其後,到了瀘州、昆明,每每只講三天。分別以曹操、孫權、諸葛亮為主題。三天的收入,當然不比十天的多。於是,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「戲碼」。唐朝的三個主題,是唐太宗、武則天、唐明皇。清朝的三個主題,是康雍乾、太平天國、慈禧。有時候,專講太平天國,便以洪秀全、石達開、曾國藩三個人為主題。(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在某一天曾經用了副刊的全張篇幅,批評我的演講,說「國民黨政府」不應該讓黎東方公開散佈擁護曾國藩,反對洪秀全的論調。其實,我對曾洪二人並未作主觀的左右袒。)
勝利以後,我在南京、貴陽、安順也講了幾次,在貴陽與安順的活動,最為重要;否則,我沒有錢「包機」,全家也就必然陷在大陸,受毛匪的磨折。在長沙變色之時,我尚在貴州大學教書,預感到貴州將為湖南之繼,就走到公路局買都勻的汽車票。公路局的人說:「沒有票了。要不要把你的名字寫下,列入候車人的名單?不過,候上半年,也輪不到你呢。」我又走到中國航空公司的辦事處。航空公司的人也說:「要不要列入候機人的名單?候上半年,也輪不到你呢。」這一位航空公司的人,以半幽默、半諷刺的口吻說:「黎先生,你若是有錢包一架飛機;倒是今天你付錢,明後天便有機。」我說:「真的麼?」他說:「真,倒是真的。因為包機是加班,不受客票先後的限制。」我說:「好。我籌足了錢,就來付包機的費用。」
包機的費用,相當於二十四張來回票,也就是四十八張飛機票的票價。(飛機上只有二十四個座位。去香港,我包;由香港回來,據他們說是「放空」。)這四十八張飛機票的錢,我在兩三個禮拜以後【後來】用九百六十張講演票的錢付清了【一架從貴陽到香港的小飛機「包機」的費用】。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,向我道賀,同時一再解釋,某職員向我建議包機之時,並無看不起我之意。他說:「的確,全國還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。您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。」我說:「那裡,那裡!胡先生才真有辦法呢。政府派了一架專機,到北平去接他出險,像我這樣的黨內名流,是『自己人』,不好意思等待政府來爭取,應該『自力更生』。不過,我所花的卻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。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,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眾的錢呢。」
為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眾,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,每天印了一張報紙,摺起來,成為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「分冊」,題為《新三國》,定價每分冊銀圓五分,一共有六個分冊。
這《新三國》,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(庇能)均重印了一次。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,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臺北版【(未訂版權買賣契約,只是租賃版權性質)】。

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。有人說我「聰明絕頂」;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,只是外表略帶秀氣而已。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,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,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。我只是懂得,像我這樣的笨人,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,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,才念得順,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刪,一篇一篇的撕了重寫,才勉強敢拿出去。我這個文章「廚子」,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,但區區微衷,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。
這部《細說三國》,不是《三國演義》或陳壽《三國志》的修訂本,也不是裴松之的《三國志注》的改編。這三部書各有千秋,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。
民國時代的盧弼,編了一部《三國志集解》,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松之。他有裴松之的耐心,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。呂思勉、祝秀俠,與姚季農、李則芬,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。
對《三國志》貢獻最大的,直至今日為止,恐怕依然是《後漢書》的作者范曄,【作補注的裴松之,】與《資治通鑒》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。我的法寶,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,不惜對讀者「和盤托出」,為的是,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《細說三國》更好的書。此外,碑銘,地方志,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,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,也都是我的法寶,乘此一併公開。
正如以前寫「細說清朝」之時一樣,我誠心懇求讀者諸君隨時寫信對我指教,我一定參照諸君的寶貴意見,於將來印行單行本之時一一加以改正。


0 意見:
張貼留言